
玻璃,除了人們習(xí)以為常的模樣,還能有哪些不一樣的形態(tài)和特質(zhì)?上海玻璃博物館的“退火”五周年特別大展“重置”11月7日開幕,并將作為常設(shè)展持續(xù)一整年。
據(jù)悉,上海玻璃博物館的“退火”項(xiàng)目始于2015年,過(guò)去五年間,博物館與一些優(yōu)秀的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家合作,將玻璃作為創(chuàng)作材料,創(chuàng)作特定場(chǎng)域的大型裝置作品,并定期舉辦展覽。與玻璃的相遇,也為藝術(shù)家們打開了一條創(chuàng)新通道。
張鼎、廖斐、楊心廣、畢蓉蓉、林天苗、劉建華、孫遜、樸慶根等八位重要的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家,不斷挑戰(zhàn)玻璃材料的邊界,撬動(dòng)其本身蘊(yùn)含的能量,為觀眾帶來(lái)了精彩的作品,而這項(xiàng)持續(xù)五年的實(shí)驗(yàn),令上海玻璃博物館成為重要的當(dāng)代藝術(shù)實(shí)踐基地,用“玻璃”鏈接了世界。
藝術(shù)家劉建華在利用玻璃創(chuàng)作的時(shí)候,堅(jiān)持追問(wèn)個(gè)體與日常的聯(lián)系,重置并打破既定概念,其矗立在廣場(chǎng)上的作品《碑》高3.4米,乍看之下,決不會(huì)有人把它的材質(zhì)當(dāng)作是玻璃,厚重的紅色調(diào),更接近于雞血石。劉建華透露,以往視覺經(jīng)驗(yàn)上的玻璃,是一種晶瑩剔透,易碎的材料,而這件作品由6厘米厚的玻璃板中空構(gòu)成,屏蔽了材質(zhì)本身給人的感受,“沒有透明度,就沒有了易碎的感覺,抽離了玻璃習(xí)慣的視覺記憶。”《碑》的創(chuàng)作耗費(fèi)了差不多一年的時(shí)間,對(duì)藝術(shù)家而言,這樣利用不同的材料進(jìn)行自由表達(dá)的機(jī)會(huì),十分難得。

在“退火“項(xiàng)目中,上海玻璃博物館鼓勵(lì)每位藝術(shù)家與陌生的材料,進(jìn)行深入交流和接觸,并以“陪伴”的態(tài)度參與項(xiàng)目的整個(gè)過(guò)程。藝術(shù)家們經(jīng)歷了對(duì)材料的陌生和誤解,最終突破自我,挑戰(zhàn)極限,創(chuàng)作出令觀者和業(yè)界都驚喜的作品。此外,該項(xiàng)目下誕生的作品,已進(jìn)入上海玻璃博物館永久收藏體系,對(duì)特色藏品體系的構(gòu)建和未來(lái)展覽的策劃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。
每一次“退火”項(xiàng)目的呈現(xiàn),都凝結(jié)著藝術(shù)家的個(gè)人風(fēng)格和獨(dú)特觀念。從張鼎對(duì)于物質(zhì)特性慣常認(rèn)知的打破、楊心廣對(duì)于玻璃與“斷腸”意象的契合、廖斐對(duì)于“平坦”意義的思辨、畢蓉蓉對(duì)于線條、塊面、色彩、結(jié)構(gòu)的再次構(gòu)建,林天苗對(duì)于個(gè)體與社會(huì)的思考,孫遜以玻璃機(jī)械裝置結(jié)合繪畫,呈現(xiàn)非線性的“空間敘事”,以及樸慶根對(duì)于“觀看”這一動(dòng)力相關(guān)且更為復(fù)雜的欲望的探索......玻璃的無(wú)限可能性被展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。曾經(jīng)習(xí)慣了使用其他材質(zhì)的藝術(shù)家,在用玻璃創(chuàng)作時(shí)都會(huì)與之博弈抗衡,而在此過(guò)程中,各自的邊界被打破重塑,進(jìn)而迸發(fā)出具有全新生命力的作品。
上海玻璃博物館創(chuàng)始人、館長(zhǎng)兼執(zhí)行總裁張琳告訴記者:“其實(shí),博物館在藝術(shù)家和制作玻璃的工匠之間充當(dāng)了一個(gè)翻譯的角色,把藝術(shù)家的語(yǔ)言翻譯給工匠,再把工匠的語(yǔ)言翻譯給藝術(shù)家,共同創(chuàng)作出符合彼此期許的作品。玻璃看起來(lái)比較日常與理性,希望這個(gè)項(xiàng)目打破固有的觀念,讓大家感覺玻璃的背后有思想。”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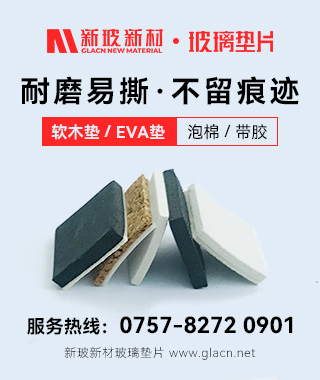




![華航材料獲2025《防火玻璃采購(gòu)?fù)扑]目錄》](http://m.guomeiren.cn/file/upload/202508/05/171706611.jpg)
![榮順祥獲2025《防火玻璃采購(gòu)?fù)扑]目錄》](http://m.guomeiren.cn/file/upload/202508/05/170828741.jpg)
![西雅特獲2025《防火玻璃采購(gòu)?fù)扑]目錄》](http://m.guomeiren.cn/file/upload/202508/05/165637771.jpg)


